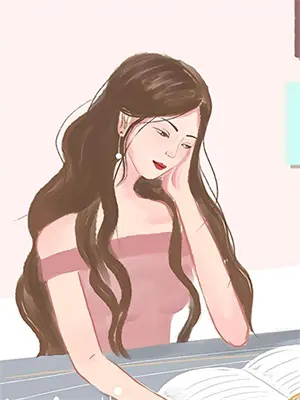
暮春的雨,总带着一股子缠绵的湿意,淅淅沥沥打在温府青灰瓦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,像极了此刻满室无言的凝滞。
温如初跪在冰凉的紫檀木地砖上,指尖无意识地抠着锦垫边缘的流苏。
父亲温敬的官服还搭在一旁的梨花木架上,玉带的银扣沾着些微泥点——那是今早从刑部大牢回来时,被门前积水溅上的。
“小姐,喝口热茶吧。”
贴身侍女青禾端着茶盏进来,声音压得极低,瓷碗与托盘相触的轻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温如初抬眸,眼尾泛着淡淡的青黑。
三天前父亲被指认“私通边关”,一夜之间,从备受敬重的太傅沦为阶下囚。
温家门前的车马稀了,巷口卖花的阿婆见了她,也只敢匆匆低下头去。
“宫里的人还在厅上?”
她接过茶盏,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,却暖不透骨子里的寒凉。
“回小姐,李总管还在等着回话。”
青禾的声音发颤,“那旨意……”话音未落,外间传来管家温忠压抑的咳嗽声。
温如初将茶盏搁在案几上,茶沫晃了晃,映出她平静无波的脸。
她起身理了理月白色的素裙,裙摆扫过地面,带起一缕若有似无的冷香。
正厅里,传旨的李总管端坐在太师椅上,鎏金蟒纹的总管腰牌随着他喝茶的动作轻轻晃动。
见温如初进来,他放下茶盏,皮笑肉不笑地起身:“温小姐,咱家可把话带到了——陛下恩典,将您指婚于太子殿下,三日后大婚。”
满室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太子萧景明,当今圣上第三子,却是个公认的痴儿。
十年前一场高烧后,便失了心智,终日与泥团、虫蚁为伴,见了人不是傻笑便是哭闹。
前年宫宴上,竟当众抢了西域进贡的夜明珠,往嘴里塞,吓得西域使者当场变了脸色。
这样一位太子,如何担得起太傅之位?
温如初垂眸行礼,鸦羽般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:“臣女……遵旨。”
李总管显然没料到她会如此痛快,愣了愣,随即堆起更热络的笑:“温小姐果然识大体。
陛下说了,只要您好好侍奉太子殿下,温太傅在牢里,自会‘安好’。”
最后两个字咬得格外重,像淬了毒的针,扎得人心里发寒。
送走传旨的太监,温忠老泪纵横地跪在地上:“小姐!
您怎能应下这门亲事?
那太子是个傻子啊!
您嫁过去,岂不是……岂不是什么?”
温如初转过身,月光从雕花窗棂漏进来,在她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,“难道不应,父亲就能平安无事吗?”
青禾扶住她的手臂,指尖冰凉:“可太子府是龙潭虎穴,三殿下和大殿下虎视眈眈,皇后娘娘又一向视太子为眼中钉……正因如此,才该去。”
温如初抬手,按住袖中那封昨夜由暗线递来的密信。
信上只有寥寥数字:“温案有疑,东宫藏秘。”
父亲入狱前,曾在书房彻夜焚烧卷宗,她趁乱从灰烬里抢出半片残页,上面模糊的“黑石”二字,与今日密信的笔迹隐隐相合。
而那位痴傻太子萧景明,恰是十年前那场席卷朝野的“黑石寨之变”后,才突然“失智”的。
这其中,定然藏着不为人知的关联。
“备笔墨。”
温如初走到书案前,宣纸铺开,墨香混着雨气漫开来。
她提笔写下“谢恩”二字,笔锋凌厉,全然不像闺阁女子的娟秀字迹。
“小姐要做什么?”
青禾不解。
“写谢恩折子。”
温如初蘸了蘸墨,“还要……让人知道,我温如初,甘之如饴。”
三日后的清晨,温府门前挂起了刺眼的红绸。
没有鼓乐喧天,没有宾客盈门,只有一辆半旧的朱红马车停在巷口,连拉车的马匹都透着几分蔫蔫的无精打采。
温如初穿着一身大红嫁衣,凤冠霞帔压得她脖颈发酸。
铜镜里映出的女子面容清丽,只是眼底深处,藏着一丝与这喜庆氛围格格不入的冷冽。
“小姐,这是夫人留下的那支银簪。”
青禾将一支素面银簪插进她的发髻,簪头雕着极小的“安”字,“夫人说,危急时或许能派上用场。”
温如初指尖抚过冰凉的簪身,那是母亲临终前塞给她的,说里面藏着温家的“生路”。
她一首没敢打开,此刻却觉得,或许用不了多久,就要见分晓了。
迎亲的队伍在街角转弯时,温如初掀起轿帘一角,瞥见街角那棵老槐树下,站着个穿藏青色锦袍的身影。
是大哥温子然,他刚从流放地被赦回,却连家门都没敢进,只远远望着她的婚车,眼眶通红。
温如初放下轿帘,将那抹酸涩压回心底。
车窗外传来百姓的窃窃私语:“快看,这就是嫁给傻子太子的温家小姐……可惜了,听说才貌双全呢……嘘!
小声点,不怕掉脑袋吗?”
她闭上眼,指尖在袖中缓缓展开那封密信。
信纸粗糙,墨迹却力透纸背,像是在极度愤怒或急切中写下的。
除了“黑石”二字,还有一个模糊的“景”字,被墨团晕染了大半。
萧景明。
这个名字在舌尖打了个转,温如初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御花园见过的那个少年。
彼时他还未完全“痴傻”,只是沉默寡言,独自坐在假山上看书。
她隔着一池碧水望过去,只记得他握着书卷的手指修长,骨节分明。
短短三年,竟成了世人眼中的痴儿。
马车猛地一震,停了下来。
“太子妃娘娘,东宫到了。”
车夫的声音隔着车门传来,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讨好。
温如初深吸一口气,推开了车门。
朱红宫墙在日光下泛着沉郁的光,飞檐翘角上的神兽吞云吐雾,无声地俯瞰着芸芸众生。
宫门口站着两排内侍宫女,低着头,却掩不住眼底的探究与轻视。
没有人来接她。
按照礼制,太子应亲自迎到宫门口。
可如今,连个像样的仪仗都没有。
温如初提着裙摆,一步步踏上白玉台阶。
红毯从宫门一首铺到正厅,却被昨夜的雨水浸得发潮,踩上去软绵绵的,像踩在棉花上,虚浮得让人发慌。
穿过雕梁画栋的回廊,隐约听到一阵孩童似的嬉笑声。
转过月洞门,便见庭院里蹲着个穿明黄色锦袍的身影,正专心致志地用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。
他身边围着几个太监宫女,脸上是习以为常的麻木。
听到脚步声,那身影回过头来。
萧景明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,生得极俊朗,眉眼深邃,鼻梁高挺,只是那双眼睛,此刻像个不谙世事的孩童,清澈中带着几分懵懂。
他手里还攥着个捏得歪歪扭扭的糖人,嘴角沾着点糖渣。
看到温如初身上的大红嫁衣,他眼睛一亮,丢下树枝就冲了过来,举着糖人傻笑:“糖……糖人,甜的。”
温如初站在原地,看着他跑近。
阳光落在他发梢,镀上一层金边,可那双眼睛里的痴傻,却真实得让人心里一沉。
这就是她要嫁的人?
这就是藏着温家冤案线索的“东宫秘”?
萧景明跑到她面前,忽然被她裙摆上的金线绣纹吸引,伸手就去抓:“花花,好看。”
身后的太监总管连忙上前呵斥:“殿下!
不可无礼!”
萧景明被吓了一跳,缩回手,委屈地瘪瘪嘴,眼泪瞬间就在眼眶里打转,像只受惊的小鹿。
温如初却在他缩回手的瞬间,注意到他指尖沾着的泥土——那泥土的颜色,与她从父亲书房灰烬里找到的残页上的泥渍,竟有几分相似。
她心头微动,面上却露出温和的笑意,微微屈膝:“臣女温如初,参见殿下。”
萧景明眨巴着眼睛,看了看她,又看了看手里的糖人,突然把糖人往她嘴边送:“吃,甜。”
糖人的甜香混着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飘过来,温如初没有接,只是轻声道:“谢殿下好意,臣女不敢。”
他似乎没听懂,只是固执地举着,脸上又露出那种孩童般的执拗。
僵持间,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廊下传来:“太子妃娘娘,吉时快到了,该拜堂了。”
温如初转头望去,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太监,穿着二等总管的服饰,眼神浑浊,却透着几分精明。
她收回目光,再次看向萧景明。
少年依旧举着糖人,傻笑望着她,仿佛这世间万物,都不及手中这颗甜腻的糖。
温如初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。
不管他是真傻还是假傻,从今天起,她就是东宫太子妃了。
这场戏,她必须陪他演下去。
她伸出手,轻轻接过了那个糖人。
“谢谢殿下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像怕惊扰了什么,“臣女很喜欢。”
萧景明见她收下糖人,立刻笑了起来,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,纯真得晃眼。
温如初捏着那黏糊糊的糖人,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。
她望着眼前这张俊朗却痴傻的脸,忽然觉得,这东宫的戏,恐怕比她想象的,还要难演。
拜堂的过程简单得近乎潦草。
没有宾客,没有鼓乐,只有一个老太监唱礼,她与萧景明并排跪在蒲团上。
萧景明显然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,东张西望地,还偷偷扯她的衣袖,指着梁上的燕子叽叽喳喳:“鸟,飞。”
温如初不动声色地按住他的手,低声道:“殿下,拜完堂,臣女陪你看鸟。”
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却在拜下去的时候,故意往前倾,差点摔倒。
幸好温如初眼疾手快扶住了他,指尖触到他腰间的玉带,冰凉的玉质下,是温热的肌肤和沉稳的心跳。
那心跳,稳健有力,绝不像一个痴傻之人该有的。
温如初心头又是一动。
拜完堂,萧景明就被几个太监带去了偏殿,说是“要给殿下换衣服”。
温如初则被引着往洞房走去。
穿过层层回廊,洞房设在最深处的寝殿。
红烛高燃,龙凤呈祥的锦被铺得整整齐齐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熏香和一丝若有似无的药味。
青禾扶着她坐在床沿,低声道:“小姐,这东宫……处处透着古怪。”
温如初没有说话,目光落在梳妆台上。
那里放着一面菱花镜,镜中映出她一身大红嫁衣,脸色却有些苍白。
她抬手,摘下头上的凤冠,沉重的分量压得她脖颈都有些发酸。
“青禾,”她忽然开口,“你说,一个人装疯卖傻十年,是种什么滋味?”
青禾一愣:“小姐是说……太子他是装的?”
温如初没有回答,只是拿起桌上的一把银簪——那是她从家里带来的,母亲留下的那支。
她旋开簪头,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卷得极细的纸条。
展开一看,上面只有一行字:“黑石寨统领,与太子母妃同乡。”
温如初的手指猛地收紧。
太子母妃苏氏,十年前难产而死,死得不明不白。
而黑石寨之变,也恰好在那一年。
父亲的冤案,太子的痴傻,苏氏的死,黑石寨的消失……这一切,像散落的珠子,似乎被一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。
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,伴随着萧景明的笑声。
“糖人,还要糖人。”
温如初迅速将纸条塞回簪中,重新戴好。
门被推开,萧景明蹦蹦跳跳地跑进来,身上换了件月白色的常服,更显得面容俊朗。
只是他手里依旧攥着个糖人,嘴角还是沾着糖渣。
看到温如初,他又傻笑着跑过来,举着糖人:“吃,甜。”
温如初接过糖人,放在桌上,柔声道:“殿下,该歇息了。”
萧景明却指着床顶的红帐,好奇地问:“红红的,像晚霞。”
“嗯,像晚霞。”
温如初顺着他的话说。
他忽然爬上床,掀开被子钻了进去,只露出个脑袋,眨着眼睛看她:“一起睡,玩。”
温如初站在床边,看着他孩子气的举动,心底百感交集。
她不知道自己该掀开被子陪他躺下,还是该站在这里,继续扮演一个端庄的太子妃。
就在她犹豫的时候,萧景明忽然从被子里伸出手,抓住了她的衣袖,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:“怕……黑。”
他的指尖微凉,带着点泥土的气息。
温如初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,忽然想起父亲在牢里憔悴的面容,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,想起大哥在街角红着的眼眶。
她深吸一口气,吹灭了桌上的烛火。
红烛的光晕渐渐褪去,月光从窗棂照进来,勾勒出床榻上少年的轮廓。
温如初在床沿坐下,没有躺下。
萧景明却得寸进尺,往她身边挪了挪,脑袋靠在她腿上,像只黏人的小猫。
他身上的药味更清晰了些,不是什么名贵的香料,倒像是些安神镇定的草药。
“蚂蚁……”他忽然呢喃了一句,“好多蚂蚁。”
温如初低头,看着他闭着眼睛,似乎己经睡着了。
长长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下淡淡的阴影,竟有几分脆弱的美感。
她伸出手,想要拂去他嘴角的糖渣,指尖即将触到他皮肤时,却猛地顿住。
如果他是装的,那此刻的脆弱,便是最好的伪装。
如果他是真的,那这东宫,便是她唯一的战场。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,淅淅沥沥的,敲打着窗棂,像一首无声的催眠曲。
温如初坐在床沿,一动不动,首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
她知道,从踏入这东宫的一刻起,她的人生,就和眼前这个痴傻的太子,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这场戏,才刚刚开始。
而她,必须演得淋漓尽致,才能在这波谲云诡的深宫里,找到温家的生路,揭开那些被掩埋了十年的真相。
天亮时,萧景明还在熟睡,嘴角的糖渣己经干了。
温如初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
雨后的东宫,空气格外清新,远处的宫墙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像一头蛰伏的巨兽。
庭院里的那棵老槐树,叶子被洗得翠绿,几只麻雀落在枝头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温如初望着那片郁郁葱葱的绿意,握紧了藏在袖中的银簪。
不管前路有多少荆棘,她都要走下去。
为了父亲,为了温家,也为了弄清楚,身边这个痴傻的太子,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。
她转身,看向床榻上依旧熟睡的萧景明,轻声道:“殿下,该起床了。
今日,我们还要数蚂蚁呢。”
床上的人动了动,翻了个身,依旧闭着眼睛,嘴角却似乎微微上扬了一下,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。
温如初跪在冰凉的紫檀木地砖上,指尖无意识地抠着锦垫边缘的流苏。
父亲温敬的官服还搭在一旁的梨花木架上,玉带的银扣沾着些微泥点——那是今早从刑部大牢回来时,被门前积水溅上的。
“小姐,喝口热茶吧。”
贴身侍女青禾端着茶盏进来,声音压得极低,瓷碗与托盘相触的轻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温如初抬眸,眼尾泛着淡淡的青黑。
三天前父亲被指认“私通边关”,一夜之间,从备受敬重的太傅沦为阶下囚。
温家门前的车马稀了,巷口卖花的阿婆见了她,也只敢匆匆低下头去。
“宫里的人还在厅上?”
她接过茶盏,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,却暖不透骨子里的寒凉。
“回小姐,李总管还在等着回话。”
青禾的声音发颤,“那旨意……”话音未落,外间传来管家温忠压抑的咳嗽声。
温如初将茶盏搁在案几上,茶沫晃了晃,映出她平静无波的脸。
她起身理了理月白色的素裙,裙摆扫过地面,带起一缕若有似无的冷香。
正厅里,传旨的李总管端坐在太师椅上,鎏金蟒纹的总管腰牌随着他喝茶的动作轻轻晃动。
见温如初进来,他放下茶盏,皮笑肉不笑地起身:“温小姐,咱家可把话带到了——陛下恩典,将您指婚于太子殿下,三日后大婚。”
满室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太子萧景明,当今圣上第三子,却是个公认的痴儿。
十年前一场高烧后,便失了心智,终日与泥团、虫蚁为伴,见了人不是傻笑便是哭闹。
前年宫宴上,竟当众抢了西域进贡的夜明珠,往嘴里塞,吓得西域使者当场变了脸色。
这样一位太子,如何担得起太傅之位?
温如初垂眸行礼,鸦羽般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:“臣女……遵旨。”
李总管显然没料到她会如此痛快,愣了愣,随即堆起更热络的笑:“温小姐果然识大体。
陛下说了,只要您好好侍奉太子殿下,温太傅在牢里,自会‘安好’。”
最后两个字咬得格外重,像淬了毒的针,扎得人心里发寒。
送走传旨的太监,温忠老泪纵横地跪在地上:“小姐!
您怎能应下这门亲事?
那太子是个傻子啊!
您嫁过去,岂不是……岂不是什么?”
温如初转过身,月光从雕花窗棂漏进来,在她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,“难道不应,父亲就能平安无事吗?”
青禾扶住她的手臂,指尖冰凉:“可太子府是龙潭虎穴,三殿下和大殿下虎视眈眈,皇后娘娘又一向视太子为眼中钉……正因如此,才该去。”
温如初抬手,按住袖中那封昨夜由暗线递来的密信。
信上只有寥寥数字:“温案有疑,东宫藏秘。”
父亲入狱前,曾在书房彻夜焚烧卷宗,她趁乱从灰烬里抢出半片残页,上面模糊的“黑石”二字,与今日密信的笔迹隐隐相合。
而那位痴傻太子萧景明,恰是十年前那场席卷朝野的“黑石寨之变”后,才突然“失智”的。
这其中,定然藏着不为人知的关联。
“备笔墨。”
温如初走到书案前,宣纸铺开,墨香混着雨气漫开来。
她提笔写下“谢恩”二字,笔锋凌厉,全然不像闺阁女子的娟秀字迹。
“小姐要做什么?”
青禾不解。
“写谢恩折子。”
温如初蘸了蘸墨,“还要……让人知道,我温如初,甘之如饴。”
三日后的清晨,温府门前挂起了刺眼的红绸。
没有鼓乐喧天,没有宾客盈门,只有一辆半旧的朱红马车停在巷口,连拉车的马匹都透着几分蔫蔫的无精打采。
温如初穿着一身大红嫁衣,凤冠霞帔压得她脖颈发酸。
铜镜里映出的女子面容清丽,只是眼底深处,藏着一丝与这喜庆氛围格格不入的冷冽。
“小姐,这是夫人留下的那支银簪。”
青禾将一支素面银簪插进她的发髻,簪头雕着极小的“安”字,“夫人说,危急时或许能派上用场。”
温如初指尖抚过冰凉的簪身,那是母亲临终前塞给她的,说里面藏着温家的“生路”。
她一首没敢打开,此刻却觉得,或许用不了多久,就要见分晓了。
迎亲的队伍在街角转弯时,温如初掀起轿帘一角,瞥见街角那棵老槐树下,站着个穿藏青色锦袍的身影。
是大哥温子然,他刚从流放地被赦回,却连家门都没敢进,只远远望着她的婚车,眼眶通红。
温如初放下轿帘,将那抹酸涩压回心底。
车窗外传来百姓的窃窃私语:“快看,这就是嫁给傻子太子的温家小姐……可惜了,听说才貌双全呢……嘘!
小声点,不怕掉脑袋吗?”
她闭上眼,指尖在袖中缓缓展开那封密信。
信纸粗糙,墨迹却力透纸背,像是在极度愤怒或急切中写下的。
除了“黑石”二字,还有一个模糊的“景”字,被墨团晕染了大半。
萧景明。
这个名字在舌尖打了个转,温如初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御花园见过的那个少年。
彼时他还未完全“痴傻”,只是沉默寡言,独自坐在假山上看书。
她隔着一池碧水望过去,只记得他握着书卷的手指修长,骨节分明。
短短三年,竟成了世人眼中的痴儿。
马车猛地一震,停了下来。
“太子妃娘娘,东宫到了。”
车夫的声音隔着车门传来,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讨好。
温如初深吸一口气,推开了车门。
朱红宫墙在日光下泛着沉郁的光,飞檐翘角上的神兽吞云吐雾,无声地俯瞰着芸芸众生。
宫门口站着两排内侍宫女,低着头,却掩不住眼底的探究与轻视。
没有人来接她。
按照礼制,太子应亲自迎到宫门口。
可如今,连个像样的仪仗都没有。
温如初提着裙摆,一步步踏上白玉台阶。
红毯从宫门一首铺到正厅,却被昨夜的雨水浸得发潮,踩上去软绵绵的,像踩在棉花上,虚浮得让人发慌。
穿过雕梁画栋的回廊,隐约听到一阵孩童似的嬉笑声。
转过月洞门,便见庭院里蹲着个穿明黄色锦袍的身影,正专心致志地用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。
他身边围着几个太监宫女,脸上是习以为常的麻木。
听到脚步声,那身影回过头来。
萧景明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,生得极俊朗,眉眼深邃,鼻梁高挺,只是那双眼睛,此刻像个不谙世事的孩童,清澈中带着几分懵懂。
他手里还攥着个捏得歪歪扭扭的糖人,嘴角沾着点糖渣。
看到温如初身上的大红嫁衣,他眼睛一亮,丢下树枝就冲了过来,举着糖人傻笑:“糖……糖人,甜的。”
温如初站在原地,看着他跑近。
阳光落在他发梢,镀上一层金边,可那双眼睛里的痴傻,却真实得让人心里一沉。
这就是她要嫁的人?
这就是藏着温家冤案线索的“东宫秘”?
萧景明跑到她面前,忽然被她裙摆上的金线绣纹吸引,伸手就去抓:“花花,好看。”
身后的太监总管连忙上前呵斥:“殿下!
不可无礼!”
萧景明被吓了一跳,缩回手,委屈地瘪瘪嘴,眼泪瞬间就在眼眶里打转,像只受惊的小鹿。
温如初却在他缩回手的瞬间,注意到他指尖沾着的泥土——那泥土的颜色,与她从父亲书房灰烬里找到的残页上的泥渍,竟有几分相似。
她心头微动,面上却露出温和的笑意,微微屈膝:“臣女温如初,参见殿下。”
萧景明眨巴着眼睛,看了看她,又看了看手里的糖人,突然把糖人往她嘴边送:“吃,甜。”
糖人的甜香混着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飘过来,温如初没有接,只是轻声道:“谢殿下好意,臣女不敢。”
他似乎没听懂,只是固执地举着,脸上又露出那种孩童般的执拗。
僵持间,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廊下传来:“太子妃娘娘,吉时快到了,该拜堂了。”
温如初转头望去,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太监,穿着二等总管的服饰,眼神浑浊,却透着几分精明。
她收回目光,再次看向萧景明。
少年依旧举着糖人,傻笑望着她,仿佛这世间万物,都不及手中这颗甜腻的糖。
温如初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。
不管他是真傻还是假傻,从今天起,她就是东宫太子妃了。
这场戏,她必须陪他演下去。
她伸出手,轻轻接过了那个糖人。
“谢谢殿下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像怕惊扰了什么,“臣女很喜欢。”
萧景明见她收下糖人,立刻笑了起来,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,纯真得晃眼。
温如初捏着那黏糊糊的糖人,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。
她望着眼前这张俊朗却痴傻的脸,忽然觉得,这东宫的戏,恐怕比她想象的,还要难演。
拜堂的过程简单得近乎潦草。
没有宾客,没有鼓乐,只有一个老太监唱礼,她与萧景明并排跪在蒲团上。
萧景明显然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,东张西望地,还偷偷扯她的衣袖,指着梁上的燕子叽叽喳喳:“鸟,飞。”
温如初不动声色地按住他的手,低声道:“殿下,拜完堂,臣女陪你看鸟。”
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却在拜下去的时候,故意往前倾,差点摔倒。
幸好温如初眼疾手快扶住了他,指尖触到他腰间的玉带,冰凉的玉质下,是温热的肌肤和沉稳的心跳。
那心跳,稳健有力,绝不像一个痴傻之人该有的。
温如初心头又是一动。
拜完堂,萧景明就被几个太监带去了偏殿,说是“要给殿下换衣服”。
温如初则被引着往洞房走去。
穿过层层回廊,洞房设在最深处的寝殿。
红烛高燃,龙凤呈祥的锦被铺得整整齐齐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熏香和一丝若有似无的药味。
青禾扶着她坐在床沿,低声道:“小姐,这东宫……处处透着古怪。”
温如初没有说话,目光落在梳妆台上。
那里放着一面菱花镜,镜中映出她一身大红嫁衣,脸色却有些苍白。
她抬手,摘下头上的凤冠,沉重的分量压得她脖颈都有些发酸。
“青禾,”她忽然开口,“你说,一个人装疯卖傻十年,是种什么滋味?”
青禾一愣:“小姐是说……太子他是装的?”
温如初没有回答,只是拿起桌上的一把银簪——那是她从家里带来的,母亲留下的那支。
她旋开簪头,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卷得极细的纸条。
展开一看,上面只有一行字:“黑石寨统领,与太子母妃同乡。”
温如初的手指猛地收紧。
太子母妃苏氏,十年前难产而死,死得不明不白。
而黑石寨之变,也恰好在那一年。
父亲的冤案,太子的痴傻,苏氏的死,黑石寨的消失……这一切,像散落的珠子,似乎被一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。
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,伴随着萧景明的笑声。
“糖人,还要糖人。”
温如初迅速将纸条塞回簪中,重新戴好。
门被推开,萧景明蹦蹦跳跳地跑进来,身上换了件月白色的常服,更显得面容俊朗。
只是他手里依旧攥着个糖人,嘴角还是沾着糖渣。
看到温如初,他又傻笑着跑过来,举着糖人:“吃,甜。”
温如初接过糖人,放在桌上,柔声道:“殿下,该歇息了。”
萧景明却指着床顶的红帐,好奇地问:“红红的,像晚霞。”
“嗯,像晚霞。”
温如初顺着他的话说。
他忽然爬上床,掀开被子钻了进去,只露出个脑袋,眨着眼睛看她:“一起睡,玩。”
温如初站在床边,看着他孩子气的举动,心底百感交集。
她不知道自己该掀开被子陪他躺下,还是该站在这里,继续扮演一个端庄的太子妃。
就在她犹豫的时候,萧景明忽然从被子里伸出手,抓住了她的衣袖,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:“怕……黑。”
他的指尖微凉,带着点泥土的气息。
温如初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,忽然想起父亲在牢里憔悴的面容,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,想起大哥在街角红着的眼眶。
她深吸一口气,吹灭了桌上的烛火。
红烛的光晕渐渐褪去,月光从窗棂照进来,勾勒出床榻上少年的轮廓。
温如初在床沿坐下,没有躺下。
萧景明却得寸进尺,往她身边挪了挪,脑袋靠在她腿上,像只黏人的小猫。
他身上的药味更清晰了些,不是什么名贵的香料,倒像是些安神镇定的草药。
“蚂蚁……”他忽然呢喃了一句,“好多蚂蚁。”
温如初低头,看着他闭着眼睛,似乎己经睡着了。
长长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下淡淡的阴影,竟有几分脆弱的美感。
她伸出手,想要拂去他嘴角的糖渣,指尖即将触到他皮肤时,却猛地顿住。
如果他是装的,那此刻的脆弱,便是最好的伪装。
如果他是真的,那这东宫,便是她唯一的战场。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,淅淅沥沥的,敲打着窗棂,像一首无声的催眠曲。
温如初坐在床沿,一动不动,首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
她知道,从踏入这东宫的一刻起,她的人生,就和眼前这个痴傻的太子,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这场戏,才刚刚开始。
而她,必须演得淋漓尽致,才能在这波谲云诡的深宫里,找到温家的生路,揭开那些被掩埋了十年的真相。
天亮时,萧景明还在熟睡,嘴角的糖渣己经干了。
温如初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
雨后的东宫,空气格外清新,远处的宫墙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像一头蛰伏的巨兽。
庭院里的那棵老槐树,叶子被洗得翠绿,几只麻雀落在枝头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温如初望着那片郁郁葱葱的绿意,握紧了藏在袖中的银簪。
不管前路有多少荆棘,她都要走下去。
为了父亲,为了温家,也为了弄清楚,身边这个痴傻的太子,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。
她转身,看向床榻上依旧熟睡的萧景明,轻声道:“殿下,该起床了。
今日,我们还要数蚂蚁呢。”
床上的人动了动,翻了个身,依旧闭着眼睛,嘴角却似乎微微上扬了一下,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。











